老师的书房 | 谭菲:读书之意不唯解,而在于求索之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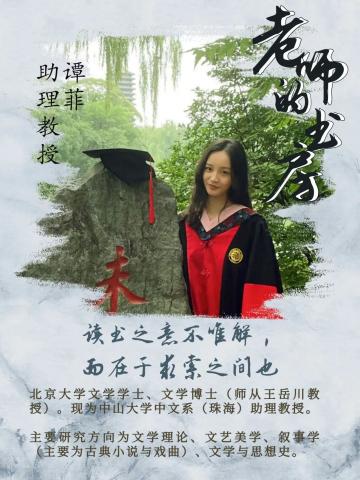
Body
编者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房,不仅是放置书籍的有限空间,更是理想的燕居之室、读书人的精神角落。置身其中,思绪已然飘至无限的大千世界,思想在此碰撞,灵感在此生发,可贵的精神气质在此熠熠生辉。
本学期,中文系(珠海)继续连载“老师的书房”专题。本期推送,邀你一起造访谭菲助理教授的阅读空间,品味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审美价值和思想之光。
01 乱序空间中的灵思
书房,常被现代人视为摆脱日常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栖息地,可谭菲老师认为自己并没有将自我寄托在这个空间中。在她看来,对书房空间的期待往往源于人们对重复性的、单向输出的“日常状态”的疲倦,而中文系学术研究是输出与输入并存的工作,在书本中就能解读出“非日常”的惊喜。
谭菲老师并不将生活局限于特定的规划,例如藏书在她看来并非是一种复杂的判断与计划,而更多出于一种“不期而遇”、“一见钟情”的选择。望眼老师的书柜,书本参差倚靠在一起,并没有严格的门类区别,这都是随拿随放的结果。“我对自己的书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脑海中可能存在改造的想法,但并不一定去实施。而在构思改造的瞬间,我就处于与未改变书房时过去的自己、心理期待中改变书房后未来的自己相处的状态中。”
与此同时,这看似“混乱”的书籍摆放并没有影响谭菲老师的读书体验,反而会带来灵感与收获。于她而言,找书的过程是一种别致的享受:在寻找的过程中与书名或作者等语词进行互动,其中无意间目之所及的字词组合、拼接能激发一些或近或远的情绪、记忆或思考碎片,这可能是诗意诞生的瞬间。
在电子化阅读兴盛的时代,谭菲老师没有对纸质书与电子书作过多意义上的划分。针对追寻纸质阅读意义的现象,谭菲老师提出:“在我们赋予纸质书意义时,它可能包含着我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留恋与期待。”当然,她并不否认电子书改变我们认知世界的可能性,但究竟选择何种阅读方式,谭菲老师认为这主要是个人选择。
02 拥抱“不唯一”的旅途
在谭菲老师看来,过往的中小学教育常使我们寻求一种方式去获取一个标准答案,导致我们在处理自身的阅读体验、阅读问题时也执着于某种“正确答案”而消解了自身的思考。她强调道:“我们不能轻易地因为自身阅读体验迥异于所谓的‘正确答案’而抛弃它们。”这些体验可能正是我们的个人历史、经验记忆和生活世界的反映,它因独一无二而弥足珍贵。
在个人阅读外,谭菲老师对于互动中的阅读体验也有自己的思考:“不同的互动环境使得我们对阅读体验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在课堂展示的小组合作中,我们因为问题集中、逻辑缜密和表达清晰的需要,可能会对各种想法采取删繁就简、整合梳理的功能性做法。而在读书会等学习小组中,我们更倾向于期待不同的想法,他者思路的参照更有利于在重读、重审中重塑自己的想法。”
面对文学阅读与理论阅读之间的关系问题,谭菲老师认为这需要回归到对理论与批评自身的思考。部分理论的建立目的并不一定是批评具体作品,这就导致该理论应用于作品的适配性程度较低。即便是那些产生于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论,也不一定适用于对所有作品的解读。
在文学作品与理论阅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或许这种期望本身就代表着对“唯一答案”的追求,即希望找到一种理论式的、正确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法。“我们常将文学作品与理论分为两个不同的事物看待,但它们可能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谭菲老师对课程体系将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划分开来造成我们对二者存在截然不同印象的现象思考道,“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领域可能只是采取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理论,它们都是服务于问题意识,而并非在各自的范畴中划分严格的边界。
谈及阅读理论书籍的手段,谭菲老师在精读原典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方法:
一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文本,即我们可以通过前人论著进入文本,通过他们的解读构建概念与思维的脉络与谱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文本因对我们的思维构成挑战而造成的阅读障碍;
二是在集体研读中收获新知,即我们可以通过小组阅读和讨论,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中获得更加丰富生动的阐释可能,并使得艰深晦涩的理论能给我们留下更加具化的印象。她形象地解释道:“你或许会想起在阳光照到某一个角度时,空气中带着属于这个季节的独特气味的某个下午,大家一起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讨论到了这个问题,甚至你会记得某个伙伴咧嘴微笑的开口度,这些画面与那些概念发生了奇妙的记忆反应,凝结在你对个人历史的反复回溯中。”
当然,这两种方法都仍然需要自己非常理性而明确的审慎和思辨,在和他人的阅读体验互动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所解所得。
在中文系学术研究与阅读紧密相连的语境下,谭菲老师认为,专业阅读与休闲阅读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区隔,反而存在一定的契合度。“即使去触碰那些看似相对遥远的、非自身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它们探讨的是同一类问题。”因此,不同的问题,亦或不同的答案,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相互启发的可能性。
03 跨越边界,通向理解
在本科求学后期,谭菲老师选择了直博。尽管在旁人看来,从本科到博士应该意味着研究视野的巨大转变,但对她而言,这种改变并不显著,一是源自本科与博士阶段就读于同一校园的熟悉感,二是与其选择的专业方向相关。
对于自己博士时期的阅读,谭菲老师并未将其与本科阶段截然区分:“我并没有因为到了博士阶段而只看我研究领域的书,即使是我身边那些有着详细规划的同学,也没有出现阅读定位、阅读范畴的巨大改变,这可能与我们人文社科的性质相关。”人文社科需要广泛阅读,从各种学科中汲取资源,这些借鉴与吸收或显见、或无形地融入到主题、行文乃至研究思路中。
而今面对学界部分反理论的声音,谭菲老师结合学术史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当词与物之间的既定关系已是司空见惯的时候,人们便会期待新的词语或概念出现,从而唤醒我们对新形势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是文学语言有陌生化的特点,文学理论也会呼唤陌生化的表述。事物通过重新命名的方式赋予意义增殖的可能,使用相对陌生的词汇去描述与定义理论,规定它的范畴,使之在易于被理解、沿用和传播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 理论并非期待永恒的固定内涵,反而仅仅是一种“权宜”。而理论恰恰是在追求这种“权宜”的阐释力和可能性,它允许自己位移,也允许自己损耗甚至失效,但却始终在历史的沉浮中试图敞开无限的可能。
随着学术词汇的增长,人文社科领域出现了诸多大众难以理解的术语。对于这些现象,谭菲老师表示这种现象并不是现代独有的,在过去也同样存在。这些术语的产生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与其所经历的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过程相关。
“面对这些或陌生或复杂的术语,我们不应设想其背后有着一个难以理解的、远超认知的存在。它在表面上建立了与日常经验区隔的高墙,但却不遗余力地试图照亮日常语言的晦暗。它并不是让我们放弃接近,相反是召唤我们去理解意义是如何在这些看似复杂的语汇中生成、移位、自反又重建的过程。”有些时候,相较于抵达某个固定答案的终点,探索的过程本身或许更能让我们有所思、有所得。
- 推荐书目 -
[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真理与方法Ⅰ、Ⅱ》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
